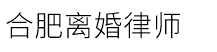关于“医药用途权利要求”的那些事儿
发布时间:2025-05-04 点击:56
一、引 言
药物的研发通常会经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投资大、风险大、难度大、周期长”是其专属特征,相对于其他技术领域而言,药物的创新非常依赖于专利的保护和激励。因此,专利保护对医药行业具有重要意义。
医药专利的权利要求分为两种,即产品权利要求与方法权利要求(或者称为物的权利要求与活动的权利要求)。其中,方法权利要求中较具价值的方法类型通常包括“产品”的制备方法以及“产品”的医药用途,这里的产品为专利法意义上的广义理解,可以包括药物活性成分、药物前体、药物中间体、原材料、药物制剂等。
就产品的医药用途而言,出于一些原因的考虑以及无法在产业上利用的情形,我国专利法第25条明确规定“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属于可授予专利权的范围。当产品的医药用途以“用于治疗疾病”“用于诊断疾病”“作为药物的应用”等技术主题申请专利时,会触发专利法第25条款规定的排除项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然而,在医药实践中,发现已知物质或者组合物的新医药用途并不比开发出新物质作为药品更容易。因此,为了保护发明人对于现有技术的创新性贡献,贯彻专利法保护创新、鼓励发明创造的立法宗旨,在我国目前的专利审查实践中,允许将发明实质为“新医药用途”的发明创造撰写成制药方法类型的权利要求作为可授予专利权的客体,如“在制备药物中的应用”、“在制备治疗某疾病的药物中的应用”等。该类型的权利要求也被称为“瑞士型权利要求”,其实质是针对物质的医药用途发明创造所做的特别规定,通过给医药用途发明创造提供必要的保护空间和制度激励来平衡社会公众与专利权人的利益[1]。
制药方法类型的权利要求旨在避开“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不能授予专利权的障碍,实为一种人为设计的权利要求撰写技巧,其实质要求保护的仍为一种医疗用途[2]。
鉴于医药用途权利要求的特殊性,在专利审查以及司法实践中评判标准往往存在争议。笔者基于专利审查指南中的相关规定以及一些司法案例针对与“瑞士型”医药用途权利要求撰写和保护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二、医药用途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常见的医药用途权利要求的限定方式包括“成分X在制备治疗疾病Y的药物中的应用”。一般而言,该类权利要求的新颖性是比较容易评判的,关键在于限定特征是否带来制药过程的区别。需要注意的是,给药剂量、给药时间间隔、给药对象、给药形式等给药特征也常见于一些制药用途权利要求中,难以避免地,引发“这些给药特征是否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构成限定”的思考。
专利审查指南中规定:对于涉及化学产品的医药用途发明,其新颖性审查应考虑“给药对象、给药方式、途径、用量及时间间隔等与使用有关的特征是否对制药过程具有限定作用,仅仅体现在用药过程中的区别特征不能使该用途具有新颖性。”
以下结合案例进行说明
案例一: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75号再审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给药剂量和时间间隔等特征属于用药过程特征,不能对药物制备过程产生实质影响,该特征不能使医药用途发明具有新颖性。
该再审裁定书中的裁判要点包括:
一是医药用途专利仅仅保护医药企业的制药行为,分析技术特征时应从制药企业的角度考虑。一般能够直接对制药过程起到限定作用的技术特征是药物的原料筛选、加工步骤、工艺流程等,而药物的给药剂量、时间间隔等给药特征,则通常仅仅体现在用药过程中,与制药过程没有直接、必然的关联性。
二是关于单位剂量与给药剂量的区分。“单位剂量”是指每一单位药物中所含活性成分的量,体现在制药过程中;“给药剂量”则是指药物的使用份量,属于药物的使用方法特征,由医生或患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并不必然影响药物的制备过程。
同样地,在无效决定第19128号中,国家知识产权局也认为,给药剂量等是医生在治疗时于用药过程中的选择,其不会对本专利制药的原料、制造方法以及适应症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于该药品的制备过程和适应症等没有影响,对该药物的制药用途来说不能构成实质性的区别。
案例二:
在默克公司专利无效案中,被请求宣告无效的独立权利要求为:17β-(N-叔丁基氨基甲酰基)-4-氮杂-5α-雄甾-1-烯-3-酮在制备适于口服给药用以治疗人的雄激素引起的脱发的药剂中的应用,其中所述的药剂包含剂量为约0.05至3.0mg的17β-(N-叔丁基氨基甲酰基)-4-氮杂-5α-雄甾-1-烯-3-酮。针对该医药用途权利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都认同“口服给药”特征能够使医药用途权利要求具有新颖性,原因在于:虽然“口服给药”涉及的是用药特征,但这一特征反过来能够对制药过程中的原料筛选步骤产生限定作用,即制药过程需要选择适合口服给药的原料。
通常来说,给药途径不同、剂型不同,相应选择药学上可以接受的辅料也不同(例如膏剂和注射剂),而辅料的选择能够对制药过程的原料筛选步骤产生影响,所以在实践过程中,给药途径这一技术特征对权利要求的限定作用一般都予以认可。
案例三:
有公司对名称为“低剂量艾替开韦制剂及其应用”的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认为涉案权利要求中“成人患者”属于给药对象,对权利要求不具有限定作用。在该案审理中,国家知识产权局(第17946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3590号判决书)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第1564号判决书)均认为“成人患者”作为给药对象,能够对制药过程产生影响,因而能够使该项权利要求具备新颖性。
理由为:给药对象不同,药物辅料和成分的含量控制也是不同的,即给药对象的限定能够对制药过程产生影响,从而对医药用途权利要求起到限定作用。
结合上述案例可知,在限定给药特征的制药用途权利要求中,根据给药特征能反推出:
制药过程具有一定特征的条件下,可以认为给药特征对制药用途权利要求具有限定作用;
反之,如果给药特征仅仅是用药过程中控制的因素而与制药过程无关,则不具有限定作用。
三、医药用途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医药用途权利要求创造性审查中常见的三种情形:
对比文件属于泛泛的综述
对比文件没有公开权利要求的医药用途,但是验证的部分指标与本案相同
权利要求对疾病进行了限定
1、对比文件属于泛泛的综述
既然,医药用途权利要求涉及已知物质,往往会存在这样一些综述性描述(例如综述性质的学术论文),这些综述性描述往往被作为对比文件用来评述医药用途的创造性。结合如下案例进行说明:
案例:
权利要求
成分X在制备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后心肌重构的药物中的应用。
说明书
通过构建急性心肌梗死动物模型,证明成分X具有改善模型动物的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提高左心室射血分数和短轴缩率等相关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后心肌重构效果。
对比文件1
综述性期刊论文描述了成分X与心血管疾病的研究进展,对成分X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概述,并对成分X在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介绍。
审查意见
根据对比文件1的记载,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合乎逻辑的推理,即可想到将成分X用于制备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后心肌重构的药物。
对此,笔者强调了如下内容:
首先,对比文件1仅客观阐述了成分X在这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中作用,并没有给出成分X对某一疾病的统一的、一致的结论。结合对比文件1的整体记载,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清楚地意识到,成分X在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是非常复杂的,并不能获得成分X的结论性作用。
再者,笔者还分析了对比文件1中与本申请内容相关之处的文献来源,并进一步分析阐述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本不会想到对患者使用含成分X的药物以提升患者体内成分X水平,毕竟临床心肌梗塞后心肌重建的评估与诊断依据之一是心脏肥大等。
最终,国家知识产权局接受了笔者的陈述,予以授权。
结合上述案例,笔者建议在阐述创造性中需要注意以下三点内容。
要点一:既然对比文件1属于综述性质的学术论文,势必会对各种学术观点、各种作证结果进行汇总,并且汇总结果往往呈现多样性,有这样的声音、也有那样的论调。并且,基于学术的严谨性,综述性质的学术论文往往少见定论性语言描述,而多用“多种作用”“双相调节作用”“有利益有弊”“影响”“调节”“可能”“潜力”“参考”之类。以上恰恰反映了医药领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正好为“我”所用。
要点二:综述性质的学术论文主要涉及对作用机理的概述,披露的作用机制比较细,具体涉及的生物指标是比较明确的,这些生物指标是否确与本申请请求保护的疾病有关联,该技术点的确认是不容易忽视的。
要点三:综述性质的学术论文是对目前相关研究的浓缩和集合,简短的一两句话可能就概述一个参考文献,恰巧此类简短概述有时会被引用以评述本申请。为此,在答审的过程中,笔者建议“溯本求源”,弄清楚该句话对应参考文献的详细方案,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掘答辩点。
2、对比文件没有公开权利要求的医药用途,但是验证的部分指标与本案相同
案例:
权利要求
成分X在制备治疗急性肾损伤的药物中的应用。
说明书
本案构建动物模型对成分X的治疗效果进行验证,部分验证结果包括:成分X能降低肾组织中生理指标1.提高肾组织中生理指标2水平。
对比文件
对比文件1涉及成分X对脑出血动物损伤保护作用的研究。结果显示:成分X能不同程度地降低损伤神经元生理指标1含量,提高生理指标2的活性。其中,生理指标1和生理指标2与防止氧化作用相关。于是,对比文件1得出结论:成分X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抗氧化损伤来起到脑保护作用。
审查意见
本申请说明书记载的试验验证所得结果也是其成分X通过抗氧化作用来发挥急性肾损伤的保护功能,其与对比文件1的作用机理是一致的,并未因为用于急性肾损伤而取得了特殊效果。
对此,笔者阐述了如下内容:
对比文件1是将成分X应用于心脑疾病,具体是脑出血,与本申请的急性肾损伤显然属于不同的临床疾病。
笔者特别强调,尽管本申请也验证了生理指标1和生理指标2.但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晓生理指标1和生理指标2并不属于常规的急性肾损伤诊疗指标。实际上,急性肾损伤的诊疗指标包括生理指标3以及尿液相关指标。对此,笔者还提供了证据。
最终,国家知识产权局接受了笔者的陈述,予以授权。
根据实务经验,笔者认为:
审查意见中常见的审查思路——就医药用途而言,药物的药理活性、作用机理等往往不乏报道,可能涉及到一些生物学指标的检测,而这些生物学指标往往又出现在其他具体疾病的报道中,如此,在这些生物学指标和其他具体疾病之间架起“桥梁”。
针对这些情形,确认这些生物学指标到底是否是某具体疾病的诊疗指标,对于能否拆除该“桥梁”是至关重要的。很多疾病都有相应的诊疗指南并且不断更新、发挥临床规范作用,这些诊疗指南往往对诊疗指标有明确记载,实际也是我们用来拆除“桥梁”的利刃。当然,其他能够拆除该“桥梁”的文献也可以很好地用于答复。
3、权利要求对疾病进行了限定
医药用途权利要求中,往往会出现“成分X在制备防治疾病Y的药物中的应用,所述疾病Y的m基因过表达”或者类似情形。笔者将结合案例说明此类情形创造性陈述中需要关注的要点。
案例:
权利要求
成分X在制备防治转移性结直肠癌的药物中的应用;所述结直肠癌为癌细胞中m基因过表达的类型;所述癌细胞为Y1细胞或Y2细胞。
对比文件
将成分X用于结直肠癌细胞Y1、Y2、Y3显效。
审查意见
m基因过表达是成分X防治转移性结直肠癌的机理,对于这种作用机理的认识过程并未改变成分X防治转移性结直肠癌这一已知疾病的类型。本申请权利要求1不具有新颖性。
对此,笔者认为:
“m基因过表达”并非是简单的机理描述,而是结直肠癌的一种具体临床类型,并且提供证据证明结直肠癌根据基因突变种类不同而分为多种类型、针对不同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治疗药物。这些证据包括《Nature》子刊文献报道、CFDA/FDA针对不同突变类型批准的相应药物的列表等。
最终,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了本案的创造性,予以授权。
根据实务经验,笔者认为:
在医药用途权利要求限定中,对疾病类型的限定是否有助于提升方案的非显而易见性,关键要弄清楚该限定到底是对机理的描述,还是通过该限定能够使该疾病区别于普通类型。如果属于前者,想必不具备新颖性;如果是后者,非显而易见性通常还有一定的论述空间。
四、结 语
笔者结合一些复审和无效的公开案例以及自身实务经验梳理、总结并探讨了如上医药用途权利要求常见问题、解析和应对建议,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示,对这类申请的实务工作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陈哲峰.《瑞士型权利要求的发展和借鉴》[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0:10.
[2]王国柱,王占军等.第二医药用途发明专利保护问题探析[J].医学与社会.第28卷第4期.2015年4月.
[3]李娜佳.给药特征类医药用途发明之新颖性审查问题研究[D].2019.
[4]张文辉.抗体相关的专利申请的中国审查实践.2017.
SA8000与ICTI的不同点
员工工伤辞职公司要怎么赔偿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过程的评价(is9000质量管理体系是什么)
iso37001反贿赂管理体系认证详细介绍
房屋租赁合同解除的时间如何确定
职工死亡抚恤金由谁继承
保健品商标注册多少钱?
如何进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申请流程及好处
药物的研发通常会经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投资大、风险大、难度大、周期长”是其专属特征,相对于其他技术领域而言,药物的创新非常依赖于专利的保护和激励。因此,专利保护对医药行业具有重要意义。
医药专利的权利要求分为两种,即产品权利要求与方法权利要求(或者称为物的权利要求与活动的权利要求)。其中,方法权利要求中较具价值的方法类型通常包括“产品”的制备方法以及“产品”的医药用途,这里的产品为专利法意义上的广义理解,可以包括药物活性成分、药物前体、药物中间体、原材料、药物制剂等。
就产品的医药用途而言,出于一些原因的考虑以及无法在产业上利用的情形,我国专利法第25条明确规定“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属于可授予专利权的范围。当产品的医药用途以“用于治疗疾病”“用于诊断疾病”“作为药物的应用”等技术主题申请专利时,会触发专利法第25条款规定的排除项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然而,在医药实践中,发现已知物质或者组合物的新医药用途并不比开发出新物质作为药品更容易。因此,为了保护发明人对于现有技术的创新性贡献,贯彻专利法保护创新、鼓励发明创造的立法宗旨,在我国目前的专利审查实践中,允许将发明实质为“新医药用途”的发明创造撰写成制药方法类型的权利要求作为可授予专利权的客体,如“在制备药物中的应用”、“在制备治疗某疾病的药物中的应用”等。该类型的权利要求也被称为“瑞士型权利要求”,其实质是针对物质的医药用途发明创造所做的特别规定,通过给医药用途发明创造提供必要的保护空间和制度激励来平衡社会公众与专利权人的利益[1]。
制药方法类型的权利要求旨在避开“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不能授予专利权的障碍,实为一种人为设计的权利要求撰写技巧,其实质要求保护的仍为一种医疗用途[2]。
鉴于医药用途权利要求的特殊性,在专利审查以及司法实践中评判标准往往存在争议。笔者基于专利审查指南中的相关规定以及一些司法案例针对与“瑞士型”医药用途权利要求撰写和保护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二、医药用途权利要求的新颖性
常见的医药用途权利要求的限定方式包括“成分X在制备治疗疾病Y的药物中的应用”。一般而言,该类权利要求的新颖性是比较容易评判的,关键在于限定特征是否带来制药过程的区别。需要注意的是,给药剂量、给药时间间隔、给药对象、给药形式等给药特征也常见于一些制药用途权利要求中,难以避免地,引发“这些给药特征是否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构成限定”的思考。
专利审查指南中规定:对于涉及化学产品的医药用途发明,其新颖性审查应考虑“给药对象、给药方式、途径、用量及时间间隔等与使用有关的特征是否对制药过程具有限定作用,仅仅体现在用药过程中的区别特征不能使该用途具有新颖性。”
以下结合案例进行说明
案例一: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75号再审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给药剂量和时间间隔等特征属于用药过程特征,不能对药物制备过程产生实质影响,该特征不能使医药用途发明具有新颖性。
该再审裁定书中的裁判要点包括:
一是医药用途专利仅仅保护医药企业的制药行为,分析技术特征时应从制药企业的角度考虑。一般能够直接对制药过程起到限定作用的技术特征是药物的原料筛选、加工步骤、工艺流程等,而药物的给药剂量、时间间隔等给药特征,则通常仅仅体现在用药过程中,与制药过程没有直接、必然的关联性。
二是关于单位剂量与给药剂量的区分。“单位剂量”是指每一单位药物中所含活性成分的量,体现在制药过程中;“给药剂量”则是指药物的使用份量,属于药物的使用方法特征,由医生或患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并不必然影响药物的制备过程。
同样地,在无效决定第19128号中,国家知识产权局也认为,给药剂量等是医生在治疗时于用药过程中的选择,其不会对本专利制药的原料、制造方法以及适应症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于该药品的制备过程和适应症等没有影响,对该药物的制药用途来说不能构成实质性的区别。
案例二:
在默克公司专利无效案中,被请求宣告无效的独立权利要求为:17β-(N-叔丁基氨基甲酰基)-4-氮杂-5α-雄甾-1-烯-3-酮在制备适于口服给药用以治疗人的雄激素引起的脱发的药剂中的应用,其中所述的药剂包含剂量为约0.05至3.0mg的17β-(N-叔丁基氨基甲酰基)-4-氮杂-5α-雄甾-1-烯-3-酮。针对该医药用途权利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都认同“口服给药”特征能够使医药用途权利要求具有新颖性,原因在于:虽然“口服给药”涉及的是用药特征,但这一特征反过来能够对制药过程中的原料筛选步骤产生限定作用,即制药过程需要选择适合口服给药的原料。
通常来说,给药途径不同、剂型不同,相应选择药学上可以接受的辅料也不同(例如膏剂和注射剂),而辅料的选择能够对制药过程的原料筛选步骤产生影响,所以在实践过程中,给药途径这一技术特征对权利要求的限定作用一般都予以认可。
案例三:
有公司对名称为“低剂量艾替开韦制剂及其应用”的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认为涉案权利要求中“成人患者”属于给药对象,对权利要求不具有限定作用。在该案审理中,国家知识产权局(第17946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3590号判决书)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第1564号判决书)均认为“成人患者”作为给药对象,能够对制药过程产生影响,因而能够使该项权利要求具备新颖性。
理由为:给药对象不同,药物辅料和成分的含量控制也是不同的,即给药对象的限定能够对制药过程产生影响,从而对医药用途权利要求起到限定作用。
结合上述案例可知,在限定给药特征的制药用途权利要求中,根据给药特征能反推出:
制药过程具有一定特征的条件下,可以认为给药特征对制药用途权利要求具有限定作用;
反之,如果给药特征仅仅是用药过程中控制的因素而与制药过程无关,则不具有限定作用。
三、医药用途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医药用途权利要求创造性审查中常见的三种情形:
对比文件属于泛泛的综述
对比文件没有公开权利要求的医药用途,但是验证的部分指标与本案相同
权利要求对疾病进行了限定
1、对比文件属于泛泛的综述
既然,医药用途权利要求涉及已知物质,往往会存在这样一些综述性描述(例如综述性质的学术论文),这些综述性描述往往被作为对比文件用来评述医药用途的创造性。结合如下案例进行说明:
案例:
权利要求
成分X在制备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后心肌重构的药物中的应用。
说明书
通过构建急性心肌梗死动物模型,证明成分X具有改善模型动物的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提高左心室射血分数和短轴缩率等相关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后心肌重构效果。
对比文件1
综述性期刊论文描述了成分X与心血管疾病的研究进展,对成分X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概述,并对成分X在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介绍。
审查意见
根据对比文件1的记载,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合乎逻辑的推理,即可想到将成分X用于制备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后心肌重构的药物。
对此,笔者强调了如下内容:
首先,对比文件1仅客观阐述了成分X在这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中作用,并没有给出成分X对某一疾病的统一的、一致的结论。结合对比文件1的整体记载,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清楚地意识到,成分X在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是非常复杂的,并不能获得成分X的结论性作用。
再者,笔者还分析了对比文件1中与本申请内容相关之处的文献来源,并进一步分析阐述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本不会想到对患者使用含成分X的药物以提升患者体内成分X水平,毕竟临床心肌梗塞后心肌重建的评估与诊断依据之一是心脏肥大等。
最终,国家知识产权局接受了笔者的陈述,予以授权。
结合上述案例,笔者建议在阐述创造性中需要注意以下三点内容。
要点一:既然对比文件1属于综述性质的学术论文,势必会对各种学术观点、各种作证结果进行汇总,并且汇总结果往往呈现多样性,有这样的声音、也有那样的论调。并且,基于学术的严谨性,综述性质的学术论文往往少见定论性语言描述,而多用“多种作用”“双相调节作用”“有利益有弊”“影响”“调节”“可能”“潜力”“参考”之类。以上恰恰反映了医药领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正好为“我”所用。
要点二:综述性质的学术论文主要涉及对作用机理的概述,披露的作用机制比较细,具体涉及的生物指标是比较明确的,这些生物指标是否确与本申请请求保护的疾病有关联,该技术点的确认是不容易忽视的。
要点三:综述性质的学术论文是对目前相关研究的浓缩和集合,简短的一两句话可能就概述一个参考文献,恰巧此类简短概述有时会被引用以评述本申请。为此,在答审的过程中,笔者建议“溯本求源”,弄清楚该句话对应参考文献的详细方案,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掘答辩点。
2、对比文件没有公开权利要求的医药用途,但是验证的部分指标与本案相同
案例:
权利要求
成分X在制备治疗急性肾损伤的药物中的应用。
说明书
本案构建动物模型对成分X的治疗效果进行验证,部分验证结果包括:成分X能降低肾组织中生理指标1.提高肾组织中生理指标2水平。
对比文件
对比文件1涉及成分X对脑出血动物损伤保护作用的研究。结果显示:成分X能不同程度地降低损伤神经元生理指标1含量,提高生理指标2的活性。其中,生理指标1和生理指标2与防止氧化作用相关。于是,对比文件1得出结论:成分X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抗氧化损伤来起到脑保护作用。
审查意见
本申请说明书记载的试验验证所得结果也是其成分X通过抗氧化作用来发挥急性肾损伤的保护功能,其与对比文件1的作用机理是一致的,并未因为用于急性肾损伤而取得了特殊效果。
对此,笔者阐述了如下内容:
对比文件1是将成分X应用于心脑疾病,具体是脑出血,与本申请的急性肾损伤显然属于不同的临床疾病。
笔者特别强调,尽管本申请也验证了生理指标1和生理指标2.但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晓生理指标1和生理指标2并不属于常规的急性肾损伤诊疗指标。实际上,急性肾损伤的诊疗指标包括生理指标3以及尿液相关指标。对此,笔者还提供了证据。
最终,国家知识产权局接受了笔者的陈述,予以授权。
根据实务经验,笔者认为:
审查意见中常见的审查思路——就医药用途而言,药物的药理活性、作用机理等往往不乏报道,可能涉及到一些生物学指标的检测,而这些生物学指标往往又出现在其他具体疾病的报道中,如此,在这些生物学指标和其他具体疾病之间架起“桥梁”。
针对这些情形,确认这些生物学指标到底是否是某具体疾病的诊疗指标,对于能否拆除该“桥梁”是至关重要的。很多疾病都有相应的诊疗指南并且不断更新、发挥临床规范作用,这些诊疗指南往往对诊疗指标有明确记载,实际也是我们用来拆除“桥梁”的利刃。当然,其他能够拆除该“桥梁”的文献也可以很好地用于答复。
3、权利要求对疾病进行了限定
医药用途权利要求中,往往会出现“成分X在制备防治疾病Y的药物中的应用,所述疾病Y的m基因过表达”或者类似情形。笔者将结合案例说明此类情形创造性陈述中需要关注的要点。
案例:
权利要求
成分X在制备防治转移性结直肠癌的药物中的应用;所述结直肠癌为癌细胞中m基因过表达的类型;所述癌细胞为Y1细胞或Y2细胞。
对比文件
将成分X用于结直肠癌细胞Y1、Y2、Y3显效。
审查意见
m基因过表达是成分X防治转移性结直肠癌的机理,对于这种作用机理的认识过程并未改变成分X防治转移性结直肠癌这一已知疾病的类型。本申请权利要求1不具有新颖性。
对此,笔者认为:
“m基因过表达”并非是简单的机理描述,而是结直肠癌的一种具体临床类型,并且提供证据证明结直肠癌根据基因突变种类不同而分为多种类型、针对不同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治疗药物。这些证据包括《Nature》子刊文献报道、CFDA/FDA针对不同突变类型批准的相应药物的列表等。
最终,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可了本案的创造性,予以授权。
根据实务经验,笔者认为:
在医药用途权利要求限定中,对疾病类型的限定是否有助于提升方案的非显而易见性,关键要弄清楚该限定到底是对机理的描述,还是通过该限定能够使该疾病区别于普通类型。如果属于前者,想必不具备新颖性;如果是后者,非显而易见性通常还有一定的论述空间。
四、结 语
笔者结合一些复审和无效的公开案例以及自身实务经验梳理、总结并探讨了如上医药用途权利要求常见问题、解析和应对建议,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示,对这类申请的实务工作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陈哲峰.《瑞士型权利要求的发展和借鉴》[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0:10.
[2]王国柱,王占军等.第二医药用途发明专利保护问题探析[J].医学与社会.第28卷第4期.2015年4月.
[3]李娜佳.给药特征类医药用途发明之新颖性审查问题研究[D].2019.
[4]张文辉.抗体相关的专利申请的中国审查实践.2017.
SA8000与ICTI的不同点
员工工伤辞职公司要怎么赔偿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过程的评价(is9000质量管理体系是什么)
iso37001反贿赂管理体系认证详细介绍
房屋租赁合同解除的时间如何确定
职工死亡抚恤金由谁继承
保健品商标注册多少钱?
如何进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申请流程及好处